酒事
 |
| 干笑两声,仰头一口,喝出那五十六度的浓烈…… |
念研究所的日子,导师经常做客,邀一桌子学生共餐。学术、文学两得意的她,不摆学者的架子,没有作家的孤傲,学生分寸无需战战兢兢把持,大伙儿也就乐于应邀。
大概缅怀小时候家境不好,兄弟姐妹们“抢吃”的时光罢,导师指望“筷子你一来,我一往,菜肴像蝗虫经过那样,瞬间被扫空”的景象。偏偏我食量极小,几度她瞥我一眼,笑着说跟我吃饭,吃不了劲头,我真是小鸟胃。
“能喝酒吗?”一次,导师忽然问我。
我面无难色,猛点头说:“能!”此后,每逢招待客人的场合,导师必拉我同去。席间,她与教授学者寒暄,从诗词谈到戏曲,从学术谈到日常,中国、马来西亚无界限。我的肚子没多少墨水,头脑没什么学问,只管拿山珍海味喂自己。当客人向导师敬酒时,我代她多喝几杯就好。这样的任务,甘之若饴。
“酒量倒是不错哦!”“审核”的结果,导师相当满意。
有趣的是,“欢玲”无意间得了个“酒”名。某次,跟导师同游北京,曾在我们这儿当客座教授的系主任,安排我到他们清华旁听一堂课。他买了一瓶二锅头酒给我,饶有兴趣地说:“欢玲啊,你提着这瓶酒边走边喝,包管路上没人敢欺负你!”寻思其意,说的是二锅头酒的厉害,兴许也带有嘲笑我的意味。我干笑两声,仰头一口,喝出那五十六度的浓烈。
日子奔走,时光如流。如今,追忆北京之旅,我在清华旁听了什么课、有幸拜见了哪位名师,早已印象模糊。倒是那瓶二锅头酒好像在胃中燃烧一般,不像是过去的事。
说到这里,请不要误信我是酒鬼。其实我没有丰富的饮酒经验。在我们家,只有年夜饭时才人手一杯,体会微醺的感觉。参加喜宴,父亲也允许我们小饮怡情。我们喝的多半是红酒,只有父亲才喝白酒。大概总是他开车的缘故吧,他喝得很节制。我曾经感到好奇,接过他手中白酒,抿一口,苦苦的,不知道爱喝白酒的人是种什么样奇怪的心理!往后便无心再喝。
我不上夜店,也不识酒趣。在宴会上,见过一名女友看到新人郎才女貌,又是接吻、又喝交杯酒,有完没完,恩爱分外明亮,她跟男友分手没有其他改变的可能,时间却浇灭不了自己的痴狂,只是束手的悲伤,于是喝得烂醉,把内心一丝不挂袒露在人前,再拖着身体像尸体离去。怯弱的我,暗中铭记:如果心灵状态欠佳,情绪悲怆,千万别在公众场合借酒精偷取温暖,它只会把自己烧成灰烬。
狮城上班那些年,几个室友工作累了,把饮酒的贪欲养大。星期五的夜晚,时而约我同去酒吧小饮。喝的是啤酒,酒精浓度低,何况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,在一起也就无所谓忧愁与烦躁,——心底的声音怕被听见。讲严厉老板的嘴脸、刻薄上司的神色,或反复描述同事间兴味的事与物,满足的笑容就像花一样,在人人脸上绽开。也谈念书熬夜赶项目的过去,在无声的世界里怀旧,时光如此美妙。劳累还在不在,就很难说。
在太阳如火球的柬埔寨,啤酒也曾与我结下一段不解之缘。吴哥城的太阳猛烈地照,古迹的范围这么大!一步步走在太阳下,迂回绕远爬上山,百年老树,雄伟寺庙,巨大佛雕……到处都是美不胜收的风景。我们简直像是从吴哥王朝时代一路走了过来,还要天荒地老地走下去,一身的汗水把衣服沾得湿濡,几乎挤得出水来。
支撑到晚饭,我提议:“点几瓶啤酒来喝怎么样?”在这个当儿,解馋不重要,让道地清甜且淡的啤酒瞬间往体内倾注凉快,才叫做痛快。这项提议是谁都要同意的。太阳大半天的施虐痕迹,顿时溶解得无影无踪。
 |
| 朗姆酒、柠檬液,加入汽水和碎冰,调出一杯杯香甜的魔液。 |
最近一次跟酒交欢,在年初二。出国游学的妹妹趁春节从澳洲回来,马来西亚终年勃发的艳阳之气把她晒得一脸红、皮肉咸。晚间长长的餐桌上,盐焗鸡、酸辣鱼、算盘子等丰盛的菜肴一扫而空后,妹妹开始献技调酒。她高举酒瓶,把澳洲带回的朗姆酒与新鲜榨汁的柠檬液快速摇壶,加入汽水和碎冰,调出一杯又一杯香甜的魔液。
“真可惜啊,这里找不到我要的那种薄荷!”妹妹不无缺憾地说。在澳洲,她学会了调酒,品酒的识见也一下子往下延伸十几年。在这里,调出的酒是什么名堂,纯正不纯正,对我们不甚重要。少了薄荷调味,众人一样畅饮。喝完一杯,目光又紧紧跟着妹妹的手,灼灼期待下一杯。在浇下不知第几杯后,我感觉全身毛发细孔舒张,有一种快活在四肢百骇流窜,仿佛呼吸也是甜的。
鸡尾酒的力量,让一家人的谈话声及欢笑声越来越大。整个家充满了喜乐。醉红在姐夫的脸上烧开,他对着MTV歌唱,伴侣也展开了歌喉。音乐与歌声愈发高昂,仿佛整个房子都跟着节奏唱起来了……
春节早已过去,我还听得兴致盎然。噢,——不!是喝得余味回甘呢。
《星洲日报·星云版》2016-04-25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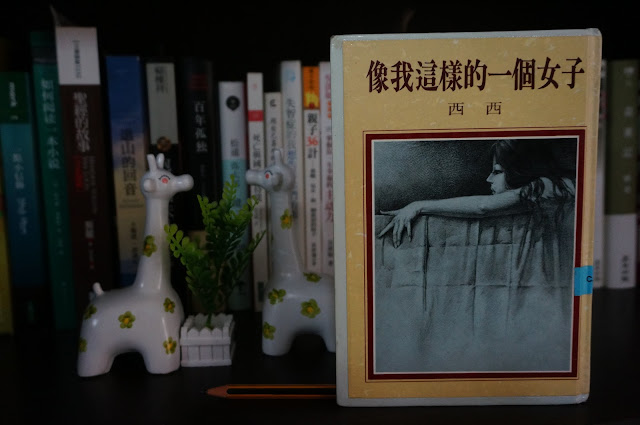
评论
发表评论